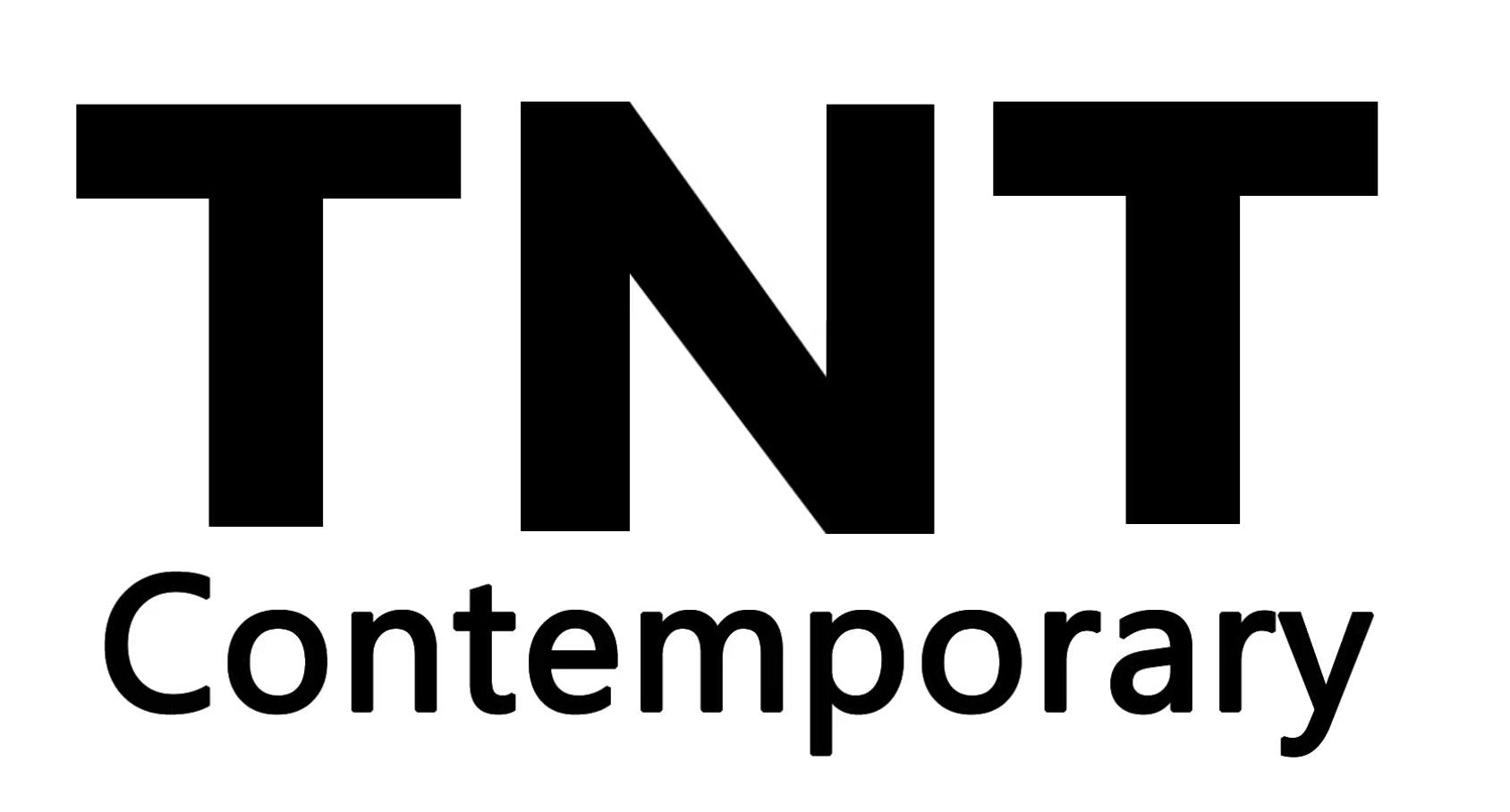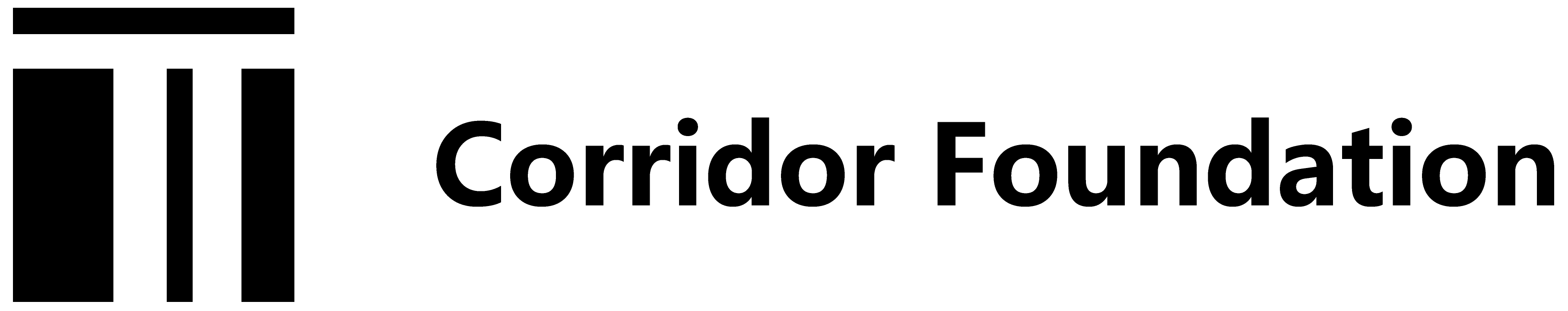oohart艺术
乌雷 | 无量之物
说明
more
马刺画廊荣幸地宣布将于秋季呈现著名艺术家乌雷(1943—2020)的首次亚洲个展“无量之物”(ULAY: The Great Journey),他是宝丽来摄影、身体和行为艺术的先驱。展览由画廊合伙人来梦馨(Sherry Lai)和乌雷基金会总监哈娜·奥斯坦·奥日博尔特(Hana Ostan Ožbolt)共同策划。乌雷与中国有着长期且深厚的关系,这片广袤和伟大的土地激发他创作了大量作品——它的风景、文化、宗教和人民给予了他一系列作品的创作灵感。这次展览是一次穿越乌雷艺术作品与生活的旅程,关注三个不同的时期: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艺术活动、他在1976年至1988年间与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的合作和他在90年代末的个人创作。 身体是一个参考、是一个起点,也是乌雷卓越运用的媒介。“我一开始使用宝丽来相机,是把镜头对准自己的——我称之为‘自动宝丽来’拍摄法——并立即发现了它的表演元素。拍摄宝丽来照片对我来说是一种表演性行为。我是在镜头前表演。”[1]在70年代早期,不仅仅限于创作方法,在创作主题上乌雷也极具先锋性,他通过无数种方式操纵宝丽来相片来捕捉自己身体的变化,例如探究身份这一主题的《白色面具》(White Mask,1973)和《乱序警句》(Anagrammatic Aphorism,1974—75)。没有观众的在场,乌雷在转瞬即逝的私密表演中探索了社会构建的性别问题——《她/他》(S'he,1973—74)中他带上了半男半女的面貌,在《修整伤痕》(Retouching Bruises,1975)中他更关注摄影如何游走于真实和虚幻之间。 自1976年至1988年,乌雷和当时的伴侣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合作。他们在爱情和工作上强烈的共生关系持续了12年。乌雷不再深挖性别问题,而是与阿布拉莫维奇一起用前卫的行为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,将彼此推向新的、甚至更加极端的、无人涉足的领域,创作挑战情感和身体的作品,考验身体和精神的能力,质疑传统的性别气质。通过他们的行为表演,他们无可争议地在行为艺术史上独树一帜。马刺画廊将展出他们标志性的表演《静止能量》(Rest Energy,1980)。在四分钟的时间里,乌雷持箭、阿布拉莫维奇持弓,他们身体倾斜以身体的重量将弓拉满;箭头直指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。两个麦克风记录了他们的心跳和呼吸声,随着这场关于完全彻底的信任的表演的进行,他们的心跳和呼吸也越来越强烈。宝丽来系列作品《星期三—星期六》(Wednesday–Saturday,1987)与他们表演实践相辅相承,专注于意识状态、精神能量、超凡的冥想和非语言交流。 1986年,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第一次访问中国。在早期的旅行计划中,这对情侣打算在长城中心结婚,但旅途最后他们用一个拥抱结束了他们的关系。在不朽的作品《情人·长城》(The Lovers: The Great Wall Walk,1988)中,他们从长城的两端相向步行了90天——当时这是一个尚没有任何西方人完成的旅程。在与中国政府进行了八年的谈判并为该项目筹集资金后,艺术家们获得了进行这项表演作品的许可。阿布拉莫维奇从长城的东端(渤海之滨的山海关)开始向西行走;乌雷从长城的西端(戈壁滩西南的嘉峪关)向东行走。两人持续向对方走去的两千公里中,他们也记录了这场旅程。展览将展出乌雷的宝丽来照片《中国——长城沿线》(China – Along the Great Wall,1986—1989),它们记录了沿途风景与他一路所遇之人,以及他当时的私密日记。受长城建筑启发的大型铝制门状雕塑《门,98》(Mén, 98,1988—89)也将展出,这是艺术家极少数量的雕塑作品之一。 1988年6月27日,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在陕西省神木市的二郎山相遇。长城漫步,最初是为了确认他们的爱情,最终却成为这段20世纪最著名而高产的艺术伙伴关系结束的标志。 《情侣》(The Lovers,1989)是乌雷在1989年创作的中型尺幅宝丽来系列作品的标题,通过纸偶的表演,在宝丽来相机前上演了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的长城漫步。乌雷当时的妻子丁小松通过操纵纸偶来解释这个故事,并为表演增加了新的参考层次。最后一幕是丁小松点燃了纸人,暗示了他们关系的结束,同时也宣告了乌雷生活新篇章的开启。 探索宝丽来摄影媒介的极限并从根本上融合摄影和行为表演,促使乌雷使用更大画幅的宝丽来相机,包括20 × 24英寸的相机(《情侣》和《星期三—星期六》系列)和最大的40 × 80英寸相机。此次展览将首次展出名为《低语》(Whispers,1993)的大尺幅宝丽来摄影作品(约240 × 110厘米)。在欧洲作家萨缪尔·贝克特(Samuel Beckett)和萧沆(Emil Cioran)的虚无主义文学的影响下,该系列的作品反映了乌雷的内心状态,同时也延续了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:表演性“自拍”,作为虚实象征的花瓶、死亡象征的骷髅与生命象征的水和种子。90年代中期拍摄的系列《孤挺花》(Amarilys,1997—2018)也深入了对这些主题的探索,正如乌雷所说,“它清楚地呈现了我探求的事物”。 乌雷的一生通过世界旅行游走于与不同文化和人与人的关系,探索身体与精神的状态及其发展。他对身份问题的终身考察是一个“舍却所学——忘记我那些赖以自圆其说的价值观与定论”的过程。“我期待的是更多的流动性,不再那么具体……我开始看到,一切都在不断地运动:生命在于变化。”[2]
乌雷 | 无量之物
艺术家
乌雷 ULAY
近期展览